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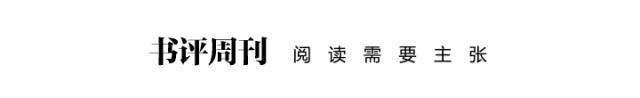
“出走或者是回来股票自己配资流程详解,都不是答案。”
当女性出走已然成为最容易引发讨论的议题之一时,作家郭玉洁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写下去。从事非虚构写作这些年,她曾以记录者的视角讲述过许多普通女人的故事。在她编发的《我是范雨素》中,我们得以看到过一个50多年不曾被生活打垮的农村女性;在《社会主义女子图鉴》中,她写下一群女性曾经如何创办女校,最终却又被时代所遗忘的过去。但在这些叙事之外,她仍然有种“不满足”,真正的生活并不只是遵循一种逻辑,她想写写那些更为复杂,或者说“更难”的主题。于是,有了这本小说集《织风暴》。
《织风暴》收录了她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写下的五篇关于普通女人的故事。不像大多数非虚构作品中呈现的那些果决的女性形象,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在生活中遭遇着各种无声的围剿,也曾在许多时刻觉察到不适,但都没有,或者说都还没有下定决心走出去。她想摊开来写写其中的那些挣扎,试图在虚构的世界中去理解每一种现实里可能的选择。先去看见,而不是先做解释。
从非虚构转向虚构,这条路她走得也并没有人们预料中那么“顺利”。她说起,很长时间里都无法说服自己“我在写小说”这件事,写了很多“不成立”的废稿,“几乎都是因为不想落入套路而变得很散,无法让人有一种阅读的乐趣”。在她看来,在虚构中写女性这件事仍然很难,但她还是觉得应该去做“难”的事。在新书出版之际,我们在北京见到了郭玉洁,和她聊了聊她想写的那种女性生活中的“复杂”,也聊起她在写作上的转变与思考。这些最终都指向了那个埋在她心里很多年的“最想写的东西”,尽管一直没动笔,但她说总有一天会写下来。

采写丨新京报记者 申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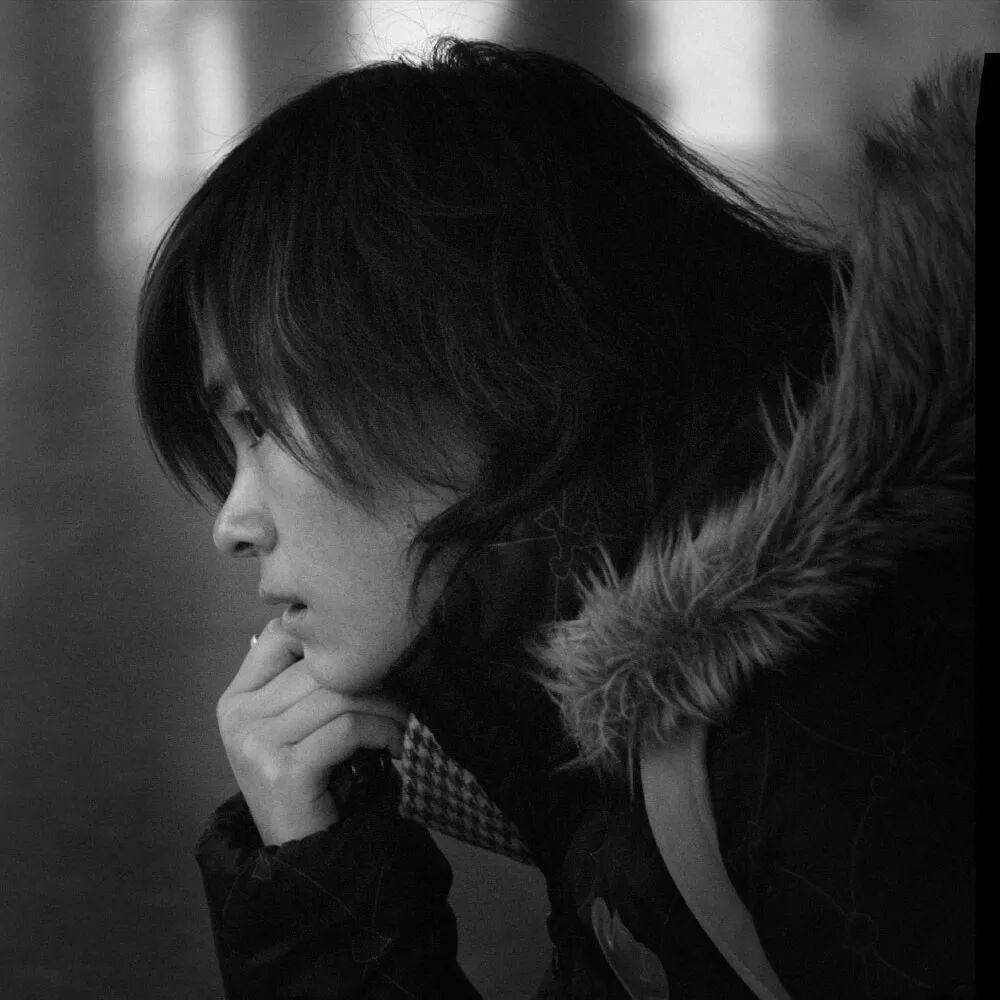
郭玉洁,作家,媒体人。先后供职于《财经》《生活》《单向街》(后更名为《单读》)《Lens》《正午》等媒体。出版有非虚构作品集《众声》,小说集《织风暴》。
落座以后,我们的对话很快转入了这次采访的正题。也许是此前多年做非虚构的经历,不论是聊起个人生活还是小说创作,郭玉洁都很少以第一人称的“我”去开启话头,她总是在讲述别人,现实中的,或者是她笔下的。这种视角也许或多或少仍然影响着她的写作本身,“从写非虚构第一天起,我们就一直在写别人,哪怕在写自己时,也还是会意识到‘别人’的存在”。
《织风暴》
作者:郭玉洁
版本:新星出版社|新经典文化 2025年10月
这种视角下,她总是下意识地在尝试“理解”。包括在这本小说集中,她旁观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的生活,写对伴侣失望的年轻妻子——她既感受过被风接纳的自由,但又“无法想象自己的身边没有他”;写孙辈出生后来大城市帮子女带娃的奶奶——她也有羞于说出口的爱好,也想为自己活一次,却总能感觉到“有种更大的力量在身后”。在这些人物背后,郭玉洁说她总还是希望还原她们各自看世界的方式。
这些关切最终都指向了她最想写的那个议题。2017年,她曾在一席的演讲《在想象的城市点亮一盏灯》中说起自己的母亲。在三年饥荒时期,甘肃是受灾最严重的省份,母亲的父母饿死在家中,母亲的姐姐考上了师范学院,一顿饭发一个馒头,她决定把妹妹接到身边,用唯一的馒头活下去。郭玉洁说,她一直很好奇母亲这代人——这群好像一夕之间突然被解放,但仍然承受着时代的灾难的女性。
然而,这个最想写的题她却至今都觉得难以动笔。她很怕这个故事讲出来就落入某种套路,也总是犹豫那个年代的故事已经被很多人讲过,她还能讲出哪些(对读者来说)不同的东西。甚至这里面也藏着她从非虚构转向虚构写作时,最难跨越的那些部分。采访中,她不止一次说起“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”,“好像没有才华”,但这些年毫无疑问的是,她仍然在写,哪怕有很多“不成立”的废稿塞进了抽屉里,她仍然觉得这件“很难”的事对她有着持续的吸引力。这些年,她一直在日常的非虚构编稿工作和私人写作之间寻找某种平衡,让自己保持“做事”的状态。她说总有一天,她要把那个“最想写的”写出来。
女孩的成长,是从经历各种“离别”开始的
新京报:这本书是五篇关于普通女人的故事。这五个故事在落笔之前,它们各自的那个“灵感”或者说最初的念头是什么?
郭玉洁:每篇都不太一样。写《观音巷》时,最初浮现的是奶奶这个形象,她的原型就是我的奶奶。像很多人一样,我小时候是奶奶隔代抚养长大的。记忆中我的奶奶一生过得很辛苦,去世也很早,对她的离世,我一直有种很难理解的感觉。那时我还很小,可能刚进入青春期,不太理解死亡具体意味着什么,就是某天回家后突然有人告诉你:“奶奶去世了。”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直到过了很久,才慢慢理解一个你很爱的人去世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。
电影《女孩》(2025)剧照。
另一个人物是小女孩鱼钩,我一直在想,女孩的成长是什么样子的?很多作家写过男孩的成长,关键的情节是性意识的萌动或者父子关系的变化,我总觉得女孩的成长不是这样的,而可能是从经历各种“离别”开始的——长辈的去世、大家族中女性亲属的出嫁,包括周围人从小就在说“等你嫁出去就如何了”。所以我想看看,一个原本无忧无虑、无法无天的女孩,如何经历这些离别,如何长大?
《滑板车》这篇则是从一个“物”开始的。某一天我出门忽然注意到,好像很多小孩都有一辆滑板车,踩着它横冲直撞,后面总是跟着一个“奶奶”。这里的奶奶和我奶奶还不太一样,她其实经历过受教育,也参加过工作,曾是这个国家的“建设者”,但到了晚年,一旦家里有小孩出生,她们好像又被默认要绑定在家庭里面。我很想写写另一个这样的“奶奶”的形象。
新京报:在《观音巷》这篇中,你以小女孩鱼钩的视角写了沙镇一个巷子里的人世日常。写一个孩子听到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、看到的家里发生的互动,那些日后可能习以为常的一切在初次接触时都曾带来过触动。在写这篇时,你也跟着鱼钩一次又一次重返自己的童年吗?
郭玉洁:写完这篇后,有好几个朋友看了说想到了《城南旧事》。它也是一个小女孩的视角,不过《城南旧事》中的小女孩相对还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,也许更容易看到其中的戏剧性,《观音巷》中更多是关于一种“心灵成长”。
由《城南旧事》改编的同名电影(1983)剧照。
在这本书中,其他几篇的主人公和我都很不像,只有这篇确实有些自己的影子。但真正开始写的时候,其实仍然不是我。因为我已经是现在的我,已经理解了很多事情,而鱼钩还留在那个年纪,我要让自己进入她的视角,一个小女孩,是如何看待世界的,就是那样一个公鸡都能成为生活中很大威胁的年纪,她不理解为什么家里会发生各种事情,大人们每天到底在聊什么,这些都不懂。这是我的一次探索,如何在成年之后又回到童年,把成年后的那些“理解”都暂且放下,用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去重新看一遍周围的世界。
新京报:你书中的很多女性都没有名字,她们是“妈妈”,是“奶奶”,好像这个称呼本身就是她们的名字。但这篇中的这个小女孩有名字,还是个“鱼钩”这样不太像名字的名字。
郭玉洁:(笑)关于名字的确想了很多。鱼钩生活的小镇是在一片沙漠地带,是很干燥的地方,但是若干年前,那里是有湖水,也有鱼的,所以这样一个名字会有一点神奇、调皮的意思,感觉很像这个女孩。
《Jungle Fly》中的两个人,我没有给他们取名字,因为人物关系比较简单,而且在我看来,这就是很多当下年轻夫妇的共同的样子。《滑板车》里也没有名字,是因为我观察到很多家庭有了小孩后,好像所有人都失去名字了,都变成了围绕孩子的一个个“职称”,爷爷奶奶爸爸妈妈,诸如此类。
新京报:这本书中其实写到了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的处境。这些年,随着你自己走到人生的中年,也陪伴目睹母亲一步步走向她的老年,你对“年龄”会有哪些不同的感受和理解吗?
郭玉洁:当我决定要写女性时,就很深地感觉到这些年国内语境的变化太大了,不同的年龄不仅意味着自然时间,年轻或是衰老,还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、世界观。我奶奶那一辈经历过饥荒和战乱,当时没有节育措施,通常都会生很多孩子;到了我母亲这代,她们经过加倍的努力获得了教育和工作的机会,但还是受到很多观念的束缚;到了我这代,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物质基础;再到我的下一代,又是另一种样子。
这些变化使得每一代看待世界、看待周围人的方式都很不同。有时候,我看一些作品写老年人,好像他们看世界、想问题的方式都和年轻人没什么区别,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当然这对我来说也是难题,我希望自己还是写出了不同时间、不同年龄的视角。
“好学生最怕写错答案”
新京报:《我去2000年》像是《观音巷》的某种“延续”。写一个中年职场女性重回大学时的记忆,此时的生活瞬间不断和当年的片段交错,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和过去对话?
郭玉洁: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,有个女同学忽然说:“我离婚了。”当时大家一下都怔住了,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但她很自然,接着说:“挺好的。真的。”这时候,忽然又有另外一个女生说:“我也离婚了。”其他女生好像慢慢反应过来了,开始纷纷举杯恭喜这两位,而桌上的其他男性好像有点不知所措,只好也举起了杯。很奇妙的场景。
那次我意识到,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,很多女性的婚姻、或者说对婚姻的感受都出现了一些问题,我想起当年她们在进入婚姻时,还是做了“很好的选择”,那时候也都很幸福,那么这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?我又发现,到这时,她们最怀念的都是校园,是读书的时光,我就想,如果真的能够回去,她们会怎么样?于是就有了这一篇。
电影《婚姻故事》(Marriage Story,2019)剧照。
新京报:当这个中年女性回到过去,她遇到了很多和她成长路径很不一样的人。那个时候的“田灵”和“阿原”,他(她)们说起自己的志向时狂野又脆弱,有很多渴望,他们想问“二十年后,他们成功了吗?这些饥饿、流离和等待都值得吗?”这也许是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曾闪过的念头。在写下这些的那一刻,你的状态是已经有了答案,还是依然渴望答案?
郭玉洁:我自己倒没有这个困惑,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饥饿、流离失所。我们这代媒体人是非常幸运的,当时处在所谓的“经济上行期”,相对自由。我们在这股浪潮中受益很多,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,像阿原这些“艺术家”,他们也没有处于过真正意义上的上行的轨道,而是过着非常边缘的生活。其实这在当年的北京,是很重要的一个艺术现象,但是这次写出来,听到很多朋友的反馈,我才知道,这段历史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。
和他们不同,这篇的主人公多丽是典型的“好学生”,她曾经很辛苦地尽量让自己每一步都不要走“错”,户口、工作、买房、小孩上学……一环扣着一环,人会在很多时候忍不住为自己过去的选择辩护,“好像只能为自己争取,还能咋办”,身处其中大多时候只是混沌赶路而已,也许要到很多年后一些选择才会浮现出轮廓。这可能就是“好学生”的课题,好学生最怕写错答案。
新京报:在这篇的末尾,多丽说她窥见了“自由以及自由的代价”,并且说“模模糊糊明白了一些新的东西:不管二十年前,还是二十年后,她所在的这一小块地方,就是现在”。可不可以展开聊聊这个感受?
郭玉洁:这和我对“穿越文学”的思考有关。我总在想,人如果穿越回去真的能改变什么,或者真的要改变什么吗?大家中年后想回到校园,真的是想做另外一个选择吗?如果在小说中让她真的做出另一个选择,那么整个世界都变化了,就不会是现在的世界,她会吗?也许更可能的还是回来面对自己的困境,面对自己的生活。
新京报:的确,你在这几篇中写到的这些女人,她们也许或多或少都在生活的某个瞬间感觉到窒息,有过逃离的念头,但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做出行动的。
郭玉洁:这可能是人的常态。其实“做选择”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想法,人大多数时候只是很本能地,或者说只能依据当时的条件去做一些行动,不一定是非常“理性”的。何况人并不是只有自己,总是会有很多其他的关系“干扰”,所以某种混沌和矛盾的状态,更像生活本来的样子。
至于出走,其实自“五四”以来,出走就是一个命题,我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,我更想追问的是“出走到哪里去”“出走之后怎么办”,也许出走,或是归来,都不是唯一的答案,归根结底,在于我们应该建造什么样的生活。
从非虚构到虚构:最难的是我找不到“成型”的逻辑
《众声》
作者:郭玉洁
版本: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1月
新京报:接下来聊聊写作吧。你在此前相关的非虚构写作和编辑中,也写过很多女性,我很好奇,同一个主题出现在不同的写作形式中,作为写作者会有哪些不同的考虑吗?
郭玉洁:关于主题,其实一开始没这么确定。但有一天我发现,当我在想一些严肃的、与时代相关的事情时,脑中就会浮现一个男性的形象,我就明白了,这是我们的文学传统赋予我的惯性,这也就意味着,即使我是一个女性,写女性也仍然是更难的,于是我决定,我应该做难的事情。
的确很难,一开始我断断续续写了很多篇,但都无法成立,很长时间内我都无法说服自己“我在写小说”这件事……
新京报: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。印象中,你写过很多有影响力的非虚构报道,同时也做了很多年的编辑,编发过像是《我是范雨素》这样的作品,对文字早已有很强的把控力。但在刚刚的短短几分钟,你却反复提到“不成立”,在你看来,那些所谓的“废稿”到底和你心中的那个“标准”差在哪里?
郭玉洁:没错,这些年我也在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。这就要回到非虚构和虚构这两种不同的文体上,的确,我在非虚构中也写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,但相比起小说,非虚构中的普通人还要“更加不普通”一些,因为你要报选题,要说服编辑、说服读者,那个人总要有特点,有故事吧?所以人物、故事已经在那了。也就是说,它总归是一个有特点的人,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逻辑,写作就是还原这个框架,填充大量细节。
而小说中的普通人,它起初甚至没有这样一个事件,生活是散落的、碎片的、矛盾的,你要寻找到一个完整的故事,可是,又不能遵循某个既有的情节框架,因为成型的事件可能意味着一个套路,我不想进入那个套路,所以,如何在散落的、碎片的、矛盾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到完整性,塑造出一个形状,又能不落俗套,这是很难的。那些我觉得“不成立”的废稿,几乎都是因为不想落入套路而变得很散,无法让人有一种阅读的乐趣。
新京报:为什么你会如此在意一篇小说是否“成型”,或者说它的“完整性”?
郭玉洁:“完整性”背后,我觉得还是一种对于生活的理解,很多生活的表面,深层是什么?今天的我们之所以如此,其实是来源于过去的很多时刻,这种联系是什么?如果没有这个完整性,我们只有碎片,只有不断更新的当下,其实是搞不清楚很多事情的。而小说,还是能提供这样的完整性。
完整性、建立叙事逻辑,富于戏剧性,让读者愿意读下去,获得阅读的愉悦感、相对完整的阅读感受,这也是我的写作追求。也许这和我的媒体经验有关,我很在意读者,不管多么专业的内容,我总希望读者能看得明白,愿意看下去,由此能形成一些共鸣和对话就更好了。当然,这不意味着去迎合读者。尊重读者和迎合读者,应该是两回事。
我很好奇母亲这代人:为什么她们看上去总“不太容易亲近”?
新京报:很多年前你曾说起,“还没有真正地开始写最想写的,类似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如何从饥荒里面过来的这样的故事”。这个“最想写的”开始动笔了吗?
郭玉洁:(笑)还没有。我仍然觉得这个题对我来说很难。那一代女性所经历的那种困难,今天的我们几乎是无法想象的。在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感知的世界之前,就还是没办法动笔。另外一个困难在于,上一代作家,像莫言、余华,他们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,已经写得很好了,如果我要写,就没有必要去重复相似的故事,那应该怎么讲呢,我还是没想好。
由《活着》改编的同名电影(1994)剧照。
新京报:也许“是否重复”也没有那么重要。相比于读者而言,这个故事也许对你,对你的家人来说是更重要的。随着家族中你母亲这代女性的陆续离开,你会感觉到有比之前更强烈的迫切感吗?
郭玉洁:也许是……这些年,我母亲的姐妹们,或是已经去世了,或是随着衰老,很多事情慢慢也都记不清了……但我好像总还是觉得,如果写不好,也是对这件事的一种“随意”。
也许,这里面更多还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这些故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?对现在的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?小时候,我就不想听母亲反反复复讲这些故事,觉得很啰嗦,忍不住想“唉,又来了”。那种感受至今一直都在,我很怕自己讲出来也给读者这样的感受。那这样就白讲了。所以关于故事的讲法,关于理解方式,我还要继续思考和探索。
新京报:我记得当年你在“一席”的那次演讲中,第一次提到想写写自己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时,当时并没有太多展开。这还是一个有些笼统和模糊的意象,你母亲这代人身上究竟是哪个面向一直如此吸引你?
郭玉洁:我很好奇的是我母亲这代人——这群好像一夕之间突然被解放,但仍然承受着时代的灾难的女性。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动,她们是如何承受的?其实细想起来,她们真的非常勇敢,我的姨妈,当年也只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,救活了当年只有6岁的我的母亲。前面我也说过,她们是新中国的建设者,她们也有很多朴素的观念,比如人要自强和平等。那是过去中国整整一代女性的面貌。与此同时,她们作为母亲,又不是传统的母亲形象,这种巨大的冲突,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种“不太容易亲近”的样子。
我一度很难理解她们,但是渐渐地,我对她们感到敬佩,也越来越好奇。她们身上的矛盾性如此巨大,这种内在的冲突到今天,也许还存在于我们身上,更年轻的女性身上。我们每一代女性,尽管有如此不同的时代际遇,也有各自的困境,但仍然有许多内在的承继,也有共同的命运。这种共同中的不同,是我想要写出来的。
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。采写:申璐;编辑:西西;校对:柳宝庆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,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
大家记得将「新京报书评周刊」设置为星标
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!
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股票自己配资流程详解
永盛金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